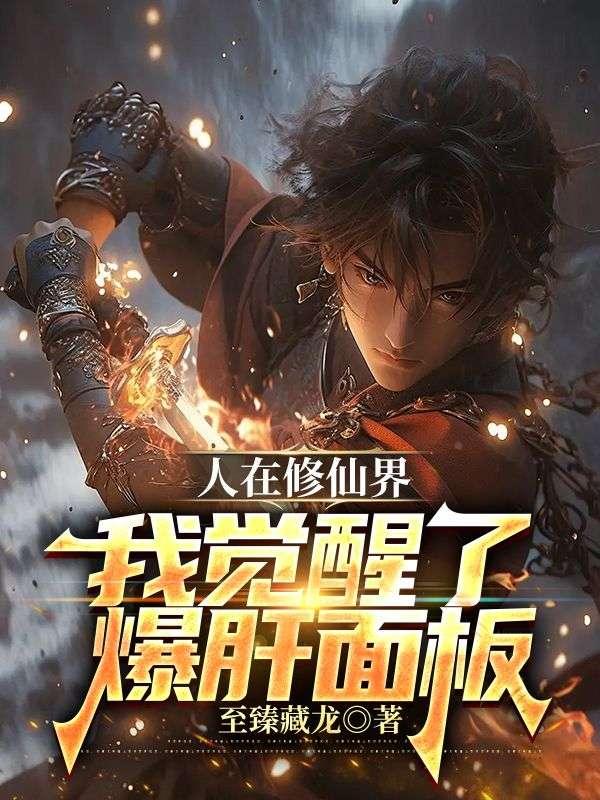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网>如果雨落下 > 5057(第11页)
5057(第11页)
怎么会觉得记录毫无意义呢?
有人说,他是天之骄子,好像任何事只要他想,都能轻松地,得偿所愿。
但他想要看懂温夏,却始终看不懂。
她好像是棵摇摇欲坠的小草,却拼命长成一棵树,扎根、茁壮、直至在春日里盎然;
她好像对谁都包容慈悲,偏偏对身处囹圄的自己下了最狠的心,她对谁都笑,偏偏对自己苛责到极致,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够好;
她好像信任他,偶尔把自己的脆弱摊开给他看,却剖得不够彻底,他最想窥探的她偏偏掩藏得最深;
她好像喜欢他,又好像不那么喜欢他……
景栩表情不爽地按下锁屏键,手机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停下。他手指放在锁屏键无意识按了又按,手机屏幕亮了又熄灭,反复好几次。
从小到大,他鲜少有这样心乱意躁的时刻。
他在这场流光溢彩的派对里再也待不下去,猛地起身,头一次,顾不上礼仪,没打招呼便独自离席。
他在空荡荡的街道瑀瑀而行,充斥着英伦优雅的街道他也无心欣赏。走到一幢维多利亚式别墅的红砖墙下,一位年迈的点灯人刚好点亮立于街边的铁艺灯盏。
他站在灯下,看着点灯人慢慢走远。
长街灯火寂寂,头顶这盏灯在冬日里发出微弱的光。
这方微弱光亮将他影子拉长,显得孤独又寂寥。
他莫名想起在树阳时,在老旧热闹的街道,她于人声鼎沸里误牵他的手,两条长长的影子在晚风中交织。
而眼下这道孤零零的影子,像一个游荡的孤魂。
好不容易在冷风中渐渐消散的那股烦躁,又在一瞬间升腾起来。
他从兜里摸出烟,低头找打火机时,正好飘了雪。
他就这么站在冷风里,看着雪缓缓坠下,目睹着雪越来越大。
长街静默。
时间仿佛静止。
大雪落在他的肩膀、发丝、黑睫上,他却一动不动。
良久。
他好像听到一句温温柔柔的“景栩你看,下雪啦”。
他循着本能回头,身后却空无一人。
这条长到没有尽头的异国街道,只有他一个人,和零星的几盏灯。
只有他一个人。
他垂眸,视线落在不远处积雪上的瞬间。
这段时间被他搁置的思念,突然泄洪般地冲出来,将他整个人席卷到窒息。
也是在这一瞬,他突然意识到。
伦敦已经这么冷了啊。
小时候他随外婆在伦敦住过几年,长大后在这里求学。
伦敦从来没这么冷过。
脑海里恰逢其时。响起被时光尘封的一句“我叫温夏,温暖的夏天”。
远在堰青的那个姑娘,是他在凛冽萧索的冬日里,唯一的夏。
他那晚在冷风和大雪里站了好久。
然后第二天。
他登上回国的飞机。
经历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,他马不停蹄赶往青外。